關于我們
聯系方式
楊國英:世上或無“溫州模式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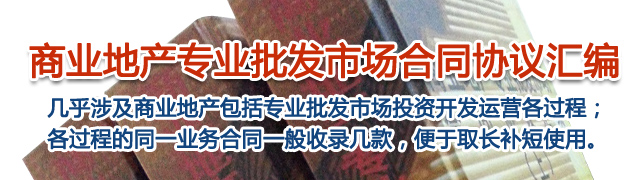 |
 |
迄今為止,對“溫州模式”能否持續,形成終極拷問的事件,共有兩次:一次是當下由高利貸引發的溫州老板“逃亡潮”;另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溫州貨的“假冒偽劣”。
1個月時間,多達近30家企業老板的逃亡,并由此導致高達萬億元貸款鏈條的可能崩潰。這場由高利貸引發的溫州地震,與20多年前溫州貨因“假冒偽劣”,而使溫州產品在全國無人問津,其嚴重性可堪一比。只不過,20年多年前的產品質量危機,最終由1987年杭州武林廣場的一把大火,重新點燃了國人對溫州的信心,溫州經濟在此后10年,持續保持著近乎全國兩倍的增長,“溫州模式”的不敗神話持續在上演。
但是,在當下高利貸的嚴重沖擊下,溫州還能一如既往地涉險而過,繼續上演“溫州模式”的不敗神話嗎?
這顯然不可能。即使逃亡在外的老板,在地方政府的維穩號召下,陸續返回溫州;即使從緊的信貸閘門,能夠對溫州部分企業網開一面,進行應急式輸血;即使溫州老板們,能夠丟棄自身的投機性,遠離高利貸的誘惑……均難以扭轉溫州經濟下行的頹勢,更難擋“溫州模式”消逝的命運。
事實上,當下溫州老板逃亡潮的引發,高利貸僅是最后一根稻草。隱身于高利貸背后,造成本輪溫州企業倒閉潮的頻現,更為本質的因素,卻是創業要素成本的企高、產業升級的迷茫,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對缺位。
這些結構性的困境,顯然無法一朝一夕予以解決。而這些阻礙溫州經濟前行的瓶頸,僅須與“蘇南模式”樣本的蘇州進行比較,其弊端就會一目了然,其嚴重性即會突顯。
就創業要素成本的企高而言,雖然溫州在工業土地、電價、水價、稅費等方面,并不比蘇州高出許多。但食品價格、房價等隱性的創業成本,溫州卻高出蘇州一大截,其食品價格高過蘇州近30%,商品房均價更是早已突破兩萬元,高出蘇州逾一倍。而之于高利貸普遍橫行的溫州,其創業資金成本之高,更令蘇州望塵末及。
再論產業升級的迷茫,我們從溫州老板輾轉全國各地,頻繁不斷的炒房、炒煤、炒蒜等,即可見其實業的虛枉之氣。以新興產業的發展為例,蘇州早于10年前即已布局高端裝備、新型平板、智能電網等新興產業,其利潤現已占到規模工業的40%以上,而這些產業溫州企業近兩年才開始涉足,且參與的規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語。此外,作為產業轉型標志之一的專利申請量,2010年溫州才剛剛破萬,僅占到同期蘇州專利申請量的15%。
正是之于經濟轉型期,地方政府產業規劃、引導的相對缺位,以及溫州民營經濟粗獷生長的野蠻基因,才造成當下溫州的上述兩大窘狀。在地方政府層面的籌劃方面,溫州要比蘇州遜色許多,蘇州早于2004年前后即啟動“騰籠換鳥”戰略,以為當地企業的轉型、升級挪騰空間,而溫州在這個環節上卻明顯言急行緩。再以基礎設施的投入比較,近10年溫州在基礎設施上的總投入,僅占到同期蘇州的1/4。而就產業園區規劃的前瞻性,以及助推其成長而言,溫州更是被蘇州拉下許多,現今為止國家級開發區溫州僅有1個,而蘇州已多達8個。此外,蘇州早于2007年就已成立百億規模的官辦創投,以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到高新企業的創建和發展之中,而溫州卻遲于去年才設立5億規模的官辦創投基金。
我們今天對溫州政府“相對缺位”的質疑,卻歷來作為“溫州模式”的靈魂受到推崇,在30年前更是賦予了溫州無與倫比的力量。彼時的溫州,以地方政府放手、不干預為特征,給予民營經濟大膽嘗試的空間,并創造了全國諸多經濟領域的第一——1982年,溫州個私企業超過10萬戶,居全國之首,占全國總數1/10;1983年,全國第一座專業市場,在溫州正式成立;1984年,全國第一座農民城,在溫州集資興辦;1987年,全國第一個關于股份制的地方規章,在溫州誕生頒布……
這種大膽放手的“政府缺位”,之于長達30年的封閉計劃經濟,無疑是令人振奮的開明之舉,亦極符合改革開放“摸著石頭過河”的精神。正是對民營經濟的不干預,激發了溫州人的創業豪情,使溫州經濟一度引領全國之先,溫州因此成為全國“自由經濟”的圣地,“溫州模式”的關健釋義亦由此而來。
但是,時過境遷,過于放任的“自由經濟”,難以保證溫州經濟的持續輝煌。在溫州民營經濟引領改革開放20年后,隨著全國各地普遍的開放搞活、招商引資,“溫州模式”的優勢不再彰顯——亦即是說,“溫州模式”在政府的放手、不干預下,給予當地民營經濟的寬松氛圍,在贏得改革開放的早期優勢,以及其后由慣性導致的高速成長后,在市場經濟的制度層面,溫州已不占據任何優勢。
2000年前后是溫州經濟下行的節點,其時為了平緩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,中央政府陸續推行了國企改革、住房改革、醫療改革和教育改革,并于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,以及2005年2月發布《非公經濟36條》。這些政策的全面實行,直接引發了直至200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。在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,市場機制之于全國已沒有邊界,溫州過于放任的“自由經濟”亦不再具有任何制度優勢。相反,在這一輪經濟賽跑中,溫州經濟的增長速度已大為遜色,其GDP增速僅為10%左右,與全國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。
但是,在2000—2008年的經濟增長周期中,蘇州的GDP平均增速卻高達15%,超出溫州的一半水平。這與此前10年兩地的經濟增速,形成了極為明顯的背反效應,1990—2000年,溫州GDP從78億元升至828億元,增加了10.6倍,而同期蘇州GDP僅增加了7.5倍,溫州在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速高出蘇州40%。
溫州與蘇州在上述兩個階段增速的背反,當然與2000年之后蘇州加大外資引進力度、溫州民資的大量外流有關。為此,學界曾用“骨肉”之喻,意指外向型經濟為特征的蘇州“國富而民窮”,而民營資本活躍的溫州“國窮而民富”。但是,這顯然是感覺之辭,事實上,隨著蘇州經濟總量的大幅上升,其與溫州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正在縮小——2000年,蘇州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為9272元,僅為同期溫州的77%,但是這一差距在2010年卻已縮小至94%,幾可忽略不計。
溫州與蘇州在“國富”層面差距的持續擴大,在“民富”層面優勢的持續減少,與其實業之根的日漸懸浮有關。而這種實體經濟的扎根不深,一旦遭遇從緊的貨幣政策、大幅減少的外需、持續上升的生產成本,必然會難以為繼。與蘇州迄今已有年產值逾百億的企業,高達100家相比,溫州尚不足10家,而年產值過千億的產業集群,蘇州已有近10個,而溫州僅有1個。
缺乏大型企業、產業集群支撐的溫州,在本輪歐美債務持續所導致的外需大幅減少,以及通脹高企生產成本加劇之下,必然會選擇匆促突圍。當這種突圍方向迷茫的心態,一旦與溫州老板普遍的投機心理、當地官權謀利的沖動相結合,則“滿城盡是高利貸”的鬧劇必然會發生。
雖然,在從緊貨幣政策、民間金融受管制的大背景下,高利貸早已成為放之全國的普遍現象,但以溫州高利貸的利率之高、規模之大、范圍之廣、波及之深而論,絕對可以冠全國之最。這就不難理解,為何企業倒閉潮、老板逃亡潮的悲劇,最終會選擇溫州來為高利貸背書。
當然,本輪由高利貸引發的溫州悲劇,在各種救急政策的出臺之后,其短期陣痛定會受到抑制,部分企業的高額債務亦會受到重組、民間金融的管制亦會逐步放開、溫州老板亦會反思自身的投機心理。但是,即使如此,溫州經濟卻難在短期內徹底恢復,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亦難以在短期內形成,政府在產業層面的規劃、布局和實施能力更難以在短期內具備,而所謂“溫州模式”的神話,卻可能就此灰飛煙滅。
任何一種經濟增長模式的成功,均與特定的政經環境密切相關,“溫州模式”之所以能領風騷20年,亦與改革開放初期差別化的政策試行有關。但當這種相對獨有的政策優勢不再,而中國經濟卻迎來新的轉型期時,“溫州模式”卻不能與時俱進,必然難逃夭折的命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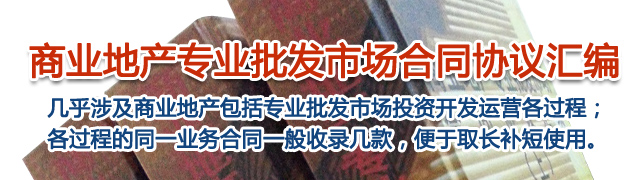 |
 |

